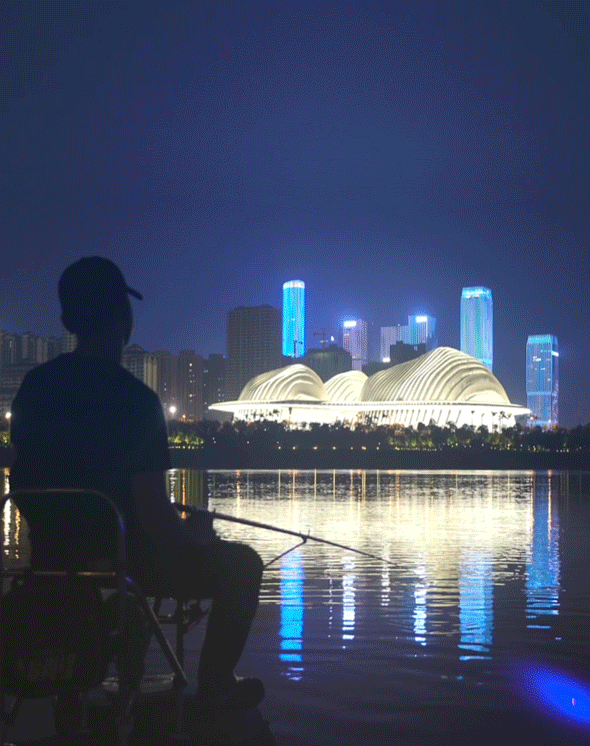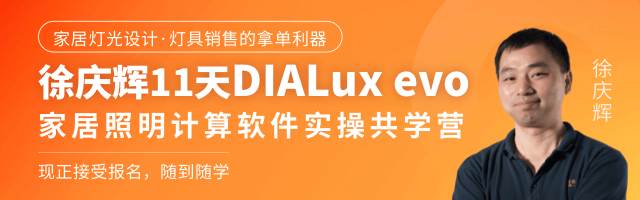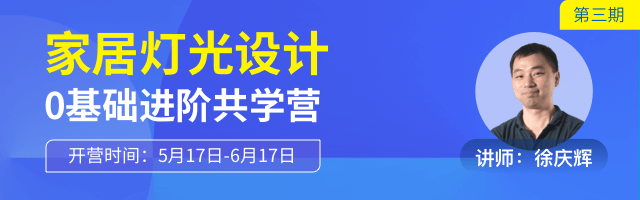注:本文内容来源于去年12月份,云知光对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所长陶震的专访,同时刊登在2019年3月第十九期《eLicht 云知光》上。
作为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所长,陶震曾经参与过不少重大项目,比如南京路步行街、昆明花博会、上海世博会等景观灯光改造项目,而外滩项目他更想要表达的是一份初心,所以他坚持为它保留一抹纯净的金黄。
从厦门到上海,两年四城,中国的城市夜色走了一个轮回。沿着外滩一直走,终于回到了人内心幸福感的所在之处。

▲雨后外滩夜景照片(拍摄时局部灯光仍在调试中)
每当想起这个梗,陶震都直呼自己是个“大忽悠”。
早在 2008年,陶震就已经在物色灯具供应商,希望为外滩建筑群定制最适合的产品。然而大家都知道,外滩夜景改造还是个没影儿的事儿,所以没人当真,陶震只能干着急。

▲1869年的外滩,图片源自网络。

▲1925年的外滩,图片源自网络。
自从 1989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上海的黄浦区,对外滩和南京路进行了灯光改造后,外滩的灯光就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的更新。那些年,热闹的南京路商业街,以“闪亮跳”的灯光闻名遐迩;而外滩建筑群气质沉静,被大面积染以金黄色,同时对建筑细节做重点投射,大片异国风情的建筑,让人如同置身巴黎塞纳河,外滩夜景一时无二。
鼎盛过后,外滩的夜景发展进入了一段很长的滞缓期。国内的夜景建设渐渐往三四线城市下沉,覆盖面越来越广,LED 的技术应用也越来越成熟。当全国城市都沉浸在一片热闹中,外滩建筑群上的传统钠灯依旧清冷地闪耀着。

▲二十世纪80年代的外滩,图片源自网络。
直到得知 2018 年首届进博会将在上海举办的消息,陶震知道必须抓住这次机会。他拿着自己多年来的研究资料,拿着自己的设计方案,开始四处奔走。“有谁能比我更懂外滩呢?”这是支撑他步履不停的唯一信念。2018年3月,外滩夜景改造项目最终顺利立项。拿到这块沉甸甸的“大石头”,他心头的大石总算可以落下。
随后的日子里,叩门问“石”的人络绎不绝。陶震深知自己想要什么,二话不说,先把技术问题抛出来,谁能解决谁就上。设计师他自己不太熟悉,业内专家推荐,凡是推荐过来的他都一一找来作品集对比研究,最后还请设计师过来出简单的设计方案并且做实地测试,几经筛选,最终敲定7家设计单位,其中只有一家来自海外――Charles Stone 主持的 FMS。
说起来,Charles Stone 也是一块有魔力的“石头”,吸引来了一群优秀设计师,毕竟,谁都不愿意放过这个跟国际灯光设计大师合作的机会。
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位于外滩建筑群外延线上的光明大厦最顶层,办公区的另一边是占地约30平的露台,露台上有一座六角形的玻璃屋,这是监控外滩灯光的控制台,从此处可以远眺外滩建筑群全貌。Charles Stone 称之为 “little room”,其他人会更形象地称呼它为“光明顶”。

▲ 从光明顶远眺外滩,摄影:eLicht 云知光
凌晨2点多,大伙儿大都回去歇息了,剩下零星几人还在案头忙着。八、九月份的上海最是闷热,蚊虫围着冷白灯管嗡嗡乱飞。
突然,一阵音乐声传来,若有若无听不真切,循声找过去,发现陶震的小办公室虚掩着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此刻,还伴随着他脚穿着拖鞋来回踱步的声音。同事们面面相觑,悄悄散去。
大家都知道,陶震喜欢音乐,喜欢研究一切跟艺术相关的学科。儿子今年6岁,正在学钢琴,他希望儿子以后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他非常坚持,必须要有一段属于外滩的主旋律。当听到青年作曲家罗威的《外滩漫步》,他就知道这乐曲契合外滩气质旋律,舒适悠扬、恬静高雅。但他提了另外一个要求:要用音乐表现建筑的语汇。
▲ 上海电视台拍摄的城市宣传片,配乐正是《外滩漫步》。
最终,音乐的后半段加入了一段探戈,表达的是古典中带有创新和变化,这是跟外滩建筑相通的。追溯每幢建筑的建造历史,可知它们本就不是“标准品”。来自西方的建筑师,在“新大陆”上的作品既传承了家乡的积淀,也适当地加入了本地元素,通过合理的搭配,使得这些建筑的意义远不止是西方文明的复制品,而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一部分。
这是陶震从建筑大师“老章明”那里了解到的。这位年过八旬的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先后修缮了百余幢近代优秀历史建筑,其中包括外滩1号、12号、15号、23号等,此次受陶震之邀,担任外滩夜景改造项目的建筑顾问。
外滩项目能把各方“能人异士”聚集在一起,陶震没少花心思,可不是吗?外滩夜景改造可不仅仅是灯光师的事儿,一定得跨界出去。
陶震永远都会记得大学毕业第一天参加工作的经历。
1996年6月30日,陶震一早来到工作单位报到,结果下班时间是凌晨12点半。因为第二天的7月1日是建军节,一些重点区域要做节庆装饰灯光。他还清楚记得,当晚10点半,大伙儿一起吃了一顿肯德基。

这个工作单位有一个名称叫霓虹灯管理所,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创办的,算是全国第一个成建制的灯光管理所。单位里的人几乎都不是做灯光出身的,有的之前做街道工作,有的搞电气安装,有的搞房产装修,还有的是来自公司的设计师。
但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算得上是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陶震常常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时尚:同事们有想法有创新能力,这很时尚;加班餐吃的不是盒饭,是肯德基,这很时尚。不过最时尚的是,他们的工作不仅能够营造城市的夜间环境,还能直接到达人的内心,留下一种叫做“幸福感”的东西。
陶震的中学时代是在黄浦区度过的,彼时最大的娱乐,便是每年9月30号晚上,沿着南京路走到西藏路,一直走到外滩,一路看灯。从来没见过一条路上能挤那么多的人,沿途霓虹灯招牌闪烁不定,迎面而来的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有时候手里的氢气球突然被挤飞掉,也不深究,高高兴兴到路边的饮料店买汽水和冰棍……

▲ 摄影:eLicht 云知光
后来,那个曾经沉浸在节日快乐气氛中的男孩来到了一个可以给无数人带去欢乐的工作岗位上,不再只是幸福感的接收者,还是创造者,帮助大家打开思路,开拓眼界。每每临近节日,他都像被上满了发条,没日没夜变着法儿去装点这座城市。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许多感动,来自团队的,来自民众的,也有来自自己的。

我不过是个摆渡人。他常常这样想。
所谓的摆渡人,是以一舟一桨,守住一河两岸。从原来的霓虹灯管理所到改名后的灯光景观管理所,为着一种莫名的信念和责任感,陶震20多年就坚守在这里:

我希望这座城市的夜景往健康和美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位置上倾注感情,守住分寸,这大概是我这一辈子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了。
我们这一两代人的美育教育是相对薄弱的,我的责任在于要做“美”的普及,让下一代人顺利接班。因为我们提供的是公共艺术产品,是美的一种形式。我不担心我们未来的设计会比国外的设计师差多少。
面前是一堵墙?不是问题,爬上去再说。上去后发现下面是一个水塘?不要紧,旁边拉根绳子就滑过去了。这就是跑酷(Parkour)。
外滩项目就像是在玩一场跑酷。是的,拿这种时尚的极限运动作比,再合适不过了。
新技术造老记忆
刚毕业进入单位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周有四天陶震都在控制中心值班,他就经常到外滩上逛。走在地上看跟在控制中心看真是不一样的视角。他常常吐槽所谓的城市鸟瞰图,我们又不是鸟,谁会从那个视角看?还是脚踏实地回到地上吧。
沿着中山东一路一直走,当太阳从浦东升起来的时候,阳光照在外滩的海关大楼上,楼顶的内膜被染上了红艳艳的光彩,然后慢慢流淌至整片建筑体上,又由朱红色调淡化为秋日里常见的枫叶色;有时候白云在天上掠过,一束或几束太阳光从云中穿梭而下,照射在某座塔楼上,像是二者在对话;满月的时候,外滩是淡淡的带一点冷冷的白。然而外滩最经典的印象,还是一抹金黄。谁都没有权力抹掉这份 2200K 钠灯色的记忆。


▲在不同太阳光照下,外滩可以呈现出“雪山日出”、“雪山夕照”等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图片源自网络。
所以陶震对光源的选择十分审慎,色温在 2200~3000K 可调控的同时还要更好地表现石材的质感,而且在灯具小型化、色温可控上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不同灯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定制改造,以追求更加精致的泛光照明效果。在此基础上,叠加模仿朝霞初升、风起云涌、皓白月光的动态演绎,使得外滩在保留原有气质底蕴的同时展现出可见可感的活力。

▲动态演绎效果,摄影:eLicht 云知光
关于动态演绎的灵感,最初来源于俄国画家艾伊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陶震对于这幅经典作品的理解是:“穿透厚重云层的阳光,给受困于风浪的人们以信心。”他试图把自然的光影效果复制到外滩夜景中,在万国建筑博览群上形成斑驳而灵动的光影。
Charles Stone 一度难以理解陶震对 2200K 的坚持,他十分清楚这些西式建筑用 2700K 的色温是最适合的,甚至曾私底下开玩笑说:“2700K 的时候,是白金汉宫;2200K 的时候,像是某个酒店?”
大家试图说服陶震:何必呢?大家都在往前走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一个跟别人对齐的项目,我们需要一个唯一的外滩。”
他的一句话便让大家折服――没有人比他更懂外滩了。

▲ 摄影:eLicht 云知光
灯光改造不只是灯光师的事情
有人会感到疑惑,陶震在外滩项目上有多大的决策权?
他心里苦笑,这不重要啊。重点是你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事情,然后为此全力(而不是“权力”)以赴。
走在外滩步道上,除了新型的人行道发光红绿灯装置格外引人注目,每幢建筑前矗立着的立杆也是十分新奇。每根立杆上集合了路灯、红绿灯、CCTV 监控录像、WIFI路由器、指示牌等多种功能器件,多个单位合作,耗时52天设计定制、安装施工完成。
真正的困难在于整合立杆所牵涉到的诸多部门的沟通协调问题,通力合作才是制胜关键。灯光改造真的不只是灯光师的事情。


▲设计团队讨论方案
外滩的灯其实不是一次就装上去的。包括选择设计师的方式也是让他们实操上阵,从临时方案到确定方案,再到局部调试,前前后后一共装了三遍。
长期以来,外滩建筑的业主们对于这位爱折腾的“古怪”所长已经很熟悉了,也有了信任的基础,但是对于这么大规模的灯光改造,他们还是觉得有所顾虑,万一做出来效果不好呢?
于是,古怪所长就带着团队反复论证落地方案,到现场跟业主一个个地去对点位,对色卡,一起做效果的验收。

▲测试灯具
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是正确的,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做,所有正向力量都会聚合到你身边。
陶震将“臻于至善”几个大字挂在单位入口处,挂在大会议室,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经常挂在嘴边。

▲办公室里除了贴满项目相关资料,还有醒目的“臻于至善”四个大字。
当外滩项目在进博会上惊艳亮相之后,他却感到很低落,因为总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时间再多一点就好了。

▲2005年的外滩夜景,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2018年的外滩夜景,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把路走绝了,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是陶震用来鼓励团队的大实话。外滩建筑历史价值之宏大,外滩所处地位之重要,人们对外滩夜景的期待值之高,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外滩的夜景改造项目上。只有真的做到(起码在当下这个阶段)让后来者“无一灯可加,无一灯可减”,才算不负这一程的智慧与汗水。
而且,最重要的是,外滩值得“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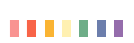

▲ 专访结束后,云知光联合创始人梁贺与陶震所长合影。
采编团队:梁贺、梁秀珊、林少莉、董银意、张辉帆
视频拍摄团队:林伟超、张国涛特别鸣谢:陶震、钱锦柯、李炜(上海市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Charles Stone(Fisher Marantz Stone 照明设计)赖雨农、刘采菱、洪嘉甫(十聿照明设计)
-欢迎留言讨论-
作者|课堂君
内容来源|云知光照明微课堂
如需转载,请后台留下公众号和微信号
投稿/合作|media@elicht.cn

▼扫描二维码,订阅杂志▼